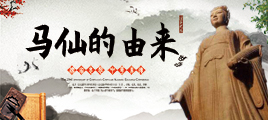作者:林加,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中小学校园是当代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空间。本文从课程的视角出发,对“非遗进校园”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讨在课程“目标、内容、形式和评价”方面取得的成果,发现问题,并提出讨论。
关键词:非遗;非遗进校园;课程;非遗传承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非遗的传承离不开非遗传承人。他们担负着“传”和“承”的双重任务;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些代表性的、被认定的传承人们应该在什么空间里传承、传播非遗文化?学校应当作为非遗传承、传播的重要空间,学生群体也应当作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的参与力量。2011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要加强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将“书法、戏曲、中华传统节日和习俗、家乡生活习俗、传统礼仪、经典民间艺术、各民族艺术”等与非遗有关的内容纳入学校教育,强调要联合非遗传承人进行相关师资培养,培养人才队伍。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让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建议的答复”》,指出要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的常态化、持续化。可见,教育部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不断强调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并逐渐推动“非遗进校园”工作。
在政策的引导下,非遗传承人进入高校开设工作室,开办课程和活动,许多专家学者也参与非遗进如高等教育校园的讨论,比如丁永详、马知遥和徐艺乙等人在其论文中讨论非遗进入高校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等内容。此外,中小学也大量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相关的实践案例的研究十分丰富。这些研究多从“非遗以何种形式进校园?进入校园的内容是哪些?进入校园的目标和依据是什么?进入校园的效果怎么样?”等角度进行讨论。这其实是将“非遗进校园”作为课程或者课程活动来进行研究。所以,本文站在公共民俗学的角度,从课程编制的视角,综述近年来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相关研究,讨论“非遗进校园”的目标、、内容、形式和评价等内容,并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近15年来,国内关于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研究主要关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和课程评价”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在课程目标方面,主要讨论了“非遗进校园”课程目标体系的建设,指出要从“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学生能力培养”两个维度出发,结合不同年龄层次的特点,设计了目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课程内容和形式方面,集中关注中小学非遗教育的实践案例,进而探讨课程内容框架的设计,探索更多适合非遗的课程形式。在课程评价方面,关注课程的成果和效果,并尝试选取一些角度来测试教学效果,探索建设评价体系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相关研究对课程内容和形式的关注度高、研究成果多,对课程目标和评价研究关注少。这就使得当下“非遗进校园”缺乏可落地、成体系的课程目标引导,导致课程评价制定无依据,缺少可操作、有效果的课程评价体系,进而导致:对课程形式的体系化认知不足,过度关注非遗校本课,而忽略别的课程形式的研究,导致不适合开设校本课的非遗项目进校困难;课程内容框架不均衡,体现为艺体类和岁时节日类非遗实践案例多、研究关注多,传统礼仪等实践案例少、研究关注少。所以,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课程目标和评价体的研究。
一、课程目标相关的研究
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评价、教学保障”等层面给出了在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意见。《纲要》指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内容要以“汉字、书法、古诗文与经典、爱国仁人志士故事、中华历史、中华传统节日和习俗、家乡生活习俗、传统礼仪、经典民间艺术、各民族艺术、生活习惯与行为规范、传统体育活动”等为主要的内容。这些内容都直接或者间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建议的答复”》,总结了近年来教育部推进“非遗进校园”所做的实践工作和制度保障,还以校园非遗传承基地、师资队伍培训、课程教育体系和组织保障与支持等内容为重点,介绍了教育部开展的非遗保护相关工作。文件最后提到教育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完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推动‘非遗进校园’常态化、规范化。”由此可见:1)教育部是把“非遗进校园”工作放在校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的。2)“非遗进校园”在教育层面缺少完善的顶层设计。3)“非遗进校园”的教育形式不够丰富,师资不足。4)“非遗进校园”在许多学校不是常态化的、规范化的。所以,讨论“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可以参考传统文化进校园课程的相关目标体系。
谭宏立足《纲要》设计了我国非遗教育传承的教学目标体系。他指出:1)在幼儿阶段进行非遗的启蒙教育,启蒙幼儿成为非遗文化的热爱者;在少年阶段进行非遗的认知教育,培养少年成为非遗文化的认同者;在青年阶段进行非遗的能力教育,培养青年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2)中小学非遗教育的目标体系既要关注教育维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又要关注文化传承维度学生在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中的角色转变。彭兆荣、路芳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等国家开展非遗教育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建设非遗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指出非遗教育体系需要一个达成共识的国家标准和程序。张莹莹在博士论文中较为细致的讨论了非遗如何结合国家颁布的美术课相关课程标准来建设课程资源系统。此外,还有诸多硕博士论文讨论如何在某一个具体学科在国家标准的指导下确定非遗相关课程的标准。但是总体而言,专门讨论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体系设计的论文比较少,民俗学者的研究参与也很少。总而言之,中小学“非遗进校园”需要体系化的课程目标。这个课程目标体系既要关注课程对非遗传承保护的意义,又要关注对校园教育尤其是学生能力培养的意义。这样的共识只是为“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方向,缺少成体系、有序列具体内容的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们从公共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民俗学理论和课程编制等相关教育学理论、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和教学实践案例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以完善目标体系的建设。
二、课程内容相关的研究
2005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了“国家+省+市+县”4级的非遗保护体系。200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文简称国家非遗名录),确立了从“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框架。截止到2018年,国家一共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将结合国家非遗名录的内容框架来梳理近年来“非遗进校园”的教育实践活动向校园引进的主要非遗内容。
本文按照研究论文的数量多少将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内容分为三类:艺体类非遗课程;岁时节日和民间文学非遗课程;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礼仪相关的非遗课程。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1)艺体类非遗项目是“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主流。艺体类非遗是指各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相关的项目。研究艺体类非遗进校园的论文数量多,研究细致。这些论文集中讨论了艺体类非遗项目与校园必修的音乐、美术、体育、劳技等课程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国家政策、国家课程标准和校园“五育并举”的角度论述艺体类非遗项目进校园的必要性;从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培养,以及实践案例的角度阐述结合的可能性。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指出当下艺体类非遗进校园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如非遗知识体系、非遗教育理论体系等。吴洪玉在论文中讨论了京剧的教育价值,列举了京剧进校园的实践探索,用具体校园案例说明了京剧在中小学开展校本课程的可能性。他认为京剧是中小学教育的语言资源,有助于提高文学素养;京剧是中小学的德育资源,有助于提高道德情操;京剧是美育资源,有助于提升审美能力。陈路芳讨论了中小学中国传统舞蹈教育对非遗舞蹈的需求,以及非遗舞蹈对中小学舞蹈教育的意义。她认为非遗舞蹈进校园不单有利于中小学美育教育的推进,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李勤总结了当下美术课程中渗透非遗内容的实践状况,指出当下美术非遗特色课程的零碎和不可复制性,介绍了以软陶为载体的特色课的开发,关注课程与美术课程标准、美育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设计了相应的教学活动和评价体系。丛密林、邓星华讨论了体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与进入中小学实践传承的路径与方法,指出了中小学进行体育文化遗产教育需要构建理论体系,概括了在中小学开展体育文化遗产教育对教育和遗产保护的意义。
(2)岁时节日和民间文学相关的非遗项目广受民俗学等相关研究者关注。岁时节日类非遗项目是指各级非遗名录中“民俗”类别下的中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气相关的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主要讨论岁时节日类非遗项目对学生德育、劳动教育和学科知识能力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岁时节日类非遗项目对校园活动和综合实践的开展、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校本课程的开发的意义与注意事项。萧放在研究中系统地阐释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指出传统节日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这为传统节日文化进入基础教育提供了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王枬、黎天业立足学校校本课程建设,详细地界定了传统节日课程的概念,论述了在基础教育中推进传统节日课程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从传统节日课程的目标、内容、类型和学习方式等角度系统地介绍了在基础教育中如何开展传统节日的教育。高扬元、米满宁立足学校的德育教育,阐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资源的开发、挖掘和整理,有助于校园德育教育的开展。成雪君、卢群赞提出将节气文化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结合,丰富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此外,还有大量硕博士论文围绕着各民族传统节日和节气文化进校园展开的的研究,涉及语文、生物、历史、美术等基础科目,如欧阳婷、付梅等等。陈建宪以中学语文教材为切入点,指出中学语文教学中民间文学的三种形式,并指出民间文学对中学语文教学而言是必要的。陈琳讨论了民间故事与语文教学的联系,并从语文教学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角度论述了民间故事进入语文教学的可能性,还从语文教师的角度简要论述了将民间文学作为课程文化资源的意义。当然还有许多学位论文讨论如何将民间文学作为资源进入中小学教育。
(3)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礼仪等非遗项目成为“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研究案例少。不过,因为这类非遗项目与学校劳动教育、美育、德育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尽管实践层面上案例较少,实践效果一般,但是也有研究者关注。齐皓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陶艺教育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意义,总结了学校对陶艺教育的需求,并从教学资源、教材、课程形式等角度提出了开展中小学陶艺教育的建议。傅小芳、丁宇红从劳动课程的政策和实施保障、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三大方面介绍了苏州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与非遗结合的情况。论文详细介绍了课程体系,并列举了苏州将“刺绣、金砖制作工艺、茶艺”等非遗内容融入劳动课程,形成区域劳动课程的特色内容。金东海、关琳介绍了当下学校礼仪教育面临的问题,指出在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当下的冲击,建议在学习西方礼仪时,要关注传统礼仪文化精髓,保留传统礼仪文化遗产,构建身份认同,避免在多元文化冲击下迷失。毕亚飞和毛岩超分别指出了传统礼仪文化如何在语文、历史教学中应用,分析了它们的价值,提出了相应的操作建议。
综合搜集的研究材料来看,艺体类非遗课程的研究数量多,多以实践案例为中心展开研究,研究者主要是一线的教育实践者,多为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和相关教育专业的硕博士。岁时节日和民间文学类非遗课程研究数量较多,多不以实践案例为中心,研究者主要是民俗学相关的研究者,相关课程案例主要是为其民俗学相关研究提供支撑材料。传统手工艺和传统礼仪相关的非遗课程研究数量少,实践案例也少。所以目前中小学“非遗进校园”课程的内容体系不均衡,这反映出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者和实践者,虽然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却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知识,具体表现为对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我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关非遗项目的类别等相关内容的了解。这也就使得“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并没有通过系统的设计和深度的考量制定均衡的课程内容框架。这就不利于在校园语境下开展全面的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
三、课程形式相关的研究
这些非遗内容是以什么形式进入校园的?就本文搜集的研究材料来看,“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形式基本分为三种:非遗校本课、融入非遗资源的校园各学科课程、非遗活动实践课。(1)非遗校本课是指学校借助非遗文化资源开设具有特色的校园选修课程。刘世军指出在开发非遗校本课程时,要科学设置课程,系统编写教材,保障校本课程能落地、有效果。杨向奎在研究中介绍了如何利用西和乞巧节结合语文课程学习的目标,设计非遗校本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吴永平、杨肖建等人以具体的案例讨论了如何将京剧文化、地方或族群文化等等编制成非遗校本课程。他们认为非遗校本课需要制定相应的学习目标,编制适合的学习内容,让学生在学习非遗文化的同时,达到德育、美育等校园教育教学目标。(2)融入非遗资源的校园各学科课程是指学校借助非遗文化资源来帮助校内学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让非遗文化资源有机融入校内学科教学。张莹莹、张思、张薇等人将非遗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独特的学科教学资源,讨论了校内的美术、语文、地理等学科如何借助非遗文化资源,在完成学科自身教学目标的同时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3)非遗活动实践课是指使用非遗文化资源进行班级和校级活动、组织学生社团、开展校外综合实践等教育教学内容的课程。王艳娟、尤吉讨论了将岁时节日非遗作为重要资源,开展学校德育美育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指出“非遗进校园”在对学生德育美育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教育具有双重意义。此外,也有学校借助非遗文化资源,为学生创办学生社团,带领学生去校外进行非遗相关的综合社会实践。在我曾经任教的清华附中,学校就有一些非遗类社团,如汉服社、诗词吟唱社、北京风俗社;年级组在节日节气点也会组织相应的德育主题活动,全校会组织端午诗会、中秋诗会、传统文化节等校园活动。除此之外,学校会使用非遗内容作为学校宣传栏、墙板报、微信公众号、校园网页等的宣传内容;还会组织学生前往非遗传承基地进行非遗相关的综合实践。
“非遗进校园”的三种基本课程形式构成了“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形式体系:德育层次为主的活动实践课,“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非遗校本课和智育层次为主的融入非遗资源的校园学科课程。这种体系化的“非遗进校园”课程形式,有助于非遗在课程形式角度对校园教育教学进行较为全面的覆盖,帮助“非遗进校园”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就本文搜集的研究材料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在开展“非遗进校园”时并没有成体系地设计非遗教育的各种课程形式,往往只有其中一两种形式。
四、课程评价体系的基本缺失
各类非遗项目借助不同形式进入校园,那么如何检测是否实现了相关的目标,教学是否有效果?这就需要讨论“非遗进校园”的课程评价体系。在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纲要》中明确指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研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标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2019年,中国教育学会制定并发布《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以下简称《指导标准》),《指导标准》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中从“评价目的、评价原则、评价方式与方法”三个角度为建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评价标准给出了建议,强调评价要以“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内容为中心”,评价要坚持“兴趣导向、持续推进、全面发展”这三个原则,评价要关注“主体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和过程的动态化”。这些建议为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评价体系和标准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建议,为后续研究和制定具体的评价框架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邓旭等人基于成都市蜀龙学校传统文化课程的实践个案提出了“基础与拓展合一”的评价体系。他们将蜀龙学校的传统文化课程评价体系分成“基础课程评价”和“拓展课程评价”两个板块,从既设计了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又设计了学校职能部门对教师的评价。从“学习投入过程与表现、个性品质发展以及学业检测成绩等”来评价学生的基础课程,从“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学习成果以及学生反思”来评价学生的拓展课程,给不同的评价项目设定了不同的分值,综合量化打分和质性评价来综合评定。这样的评价体系关注到多元主体,多维内容和多样评价方式,但是在评价内容框架的设置上对传统文化内容本身的关注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关注传统文化教育是否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理解的作用?是否对文化传承起到作用?曲雪梅在其研究中则充分考虑了区域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时,如何设计评价标准和体系去检测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她在研究中将评价体系分成了“课程的评价、实施的评价和效果的评价”。这其实是在时间线的推进上对“非遗进校园”课程的开发与设计、实施和教学成果进行评价。她给每一个阶段的评价设计了简要的内容,并强调最终的“效果的评价”一定要坚持多元评价标准。曲雪梅的研究是从课程的视角对“区域推进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设计和论述,尤其是对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的框架设计比较全面。但是在课程目标和课程评价上,似乎又仅仅只关注了“非遗进校园”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意义,忽略了对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的意义。此外,在众多研究“非遗进校园”的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并没有进行评价体系的讨论与设计,在一些专门讨论“书法”“京剧”等某一类艺术类“非遗进校园”的硕博士论文中会提及一些评价,但是大多都缺少对评价体系的探讨,缺少对评价体系的设计。
五、综述反思与建议
综合前文,从课程编制的视角出发,本文认为目前中小学“非遗进校园”存在这些问题:1)课程目标体系缺少研究和建构,导致课程缺少方向,无法使得文化传承与校园教育的目标获得双赢,影响课程的持续性;2)课程内容架构缺少总体设计,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内容集中在艺体类非遗项目,内容相对单一,影响课程的丰富性;3)课程形式的体系不清晰,形式上过度依赖非遗校本课,导致不适合校本课的项目难以入校,也无法充分发挥非遗在中小学的教育作用;4)课程评价体系的普遍缺失,导致课程有效性不可测且不可知,影响课程的持续性和常态化。对“非遗进校园”的“校园”的理解不全面,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核心原因。
“非遗进校园”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进入校园。这个“校园”不单单指校园物理空间,更是指校园语境,即当非遗进入校园这个物理空间时,要考虑非遗与校园内的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考虑非遗与校园内整个教学生态的有机联系。“非遗进校园”需要课程编制的视角,以课程或者课程活动的角色进入中小学校园。它绝不不仅仅是一场文化展演或者文化体验。所以在中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需要充分讨论和研究“课程目标体系、课程内容框架、课程形式体系和课程评价体系”的相关内容。本文建议:
第一、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体系需要关注“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和“学生能力培养”两个基本维度,民俗学和教育学者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非遗进校园”课程目标体系的建设,制定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各地校园事情的总体目标框架,对框架下的细则提供方向性建议,并积极参与具体内容制定的指导工作。
第二、做好非遗名录中非遗项目向“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转写工作,做好“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资源库的研究和建设,对专业性较高的传统礼仪等内容进行普及材料编写,为各地开展非遗各类教材的编写提供支持和建议,促进非遗不同类别的项目均衡地进入中小学校园,避免艺体类非遗过多,而其他的内容不足的现象。
第三、进一步探索并完善“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形式体系,在做好非遗校本课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活动实践课的优势,将学生带往非遗传承基地、实践基地,进行传统手工技艺等难以进入校园物理空间的非遗项目的学习。进入非遗传承基地学习本身符合教育部等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这些校外学习空间是校园语境下的校外空间,是校园教育生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校外非遗基地学习非遗,也是“非遗进校园”的重要形式。加大对非遗资源融入校内学科课程的研究,促进非遗文化与各学科的有机融合,真正做到《纲要》呼吁的学科课程全覆盖,将教育内容体现到德育、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主要课程中去。只有让非遗进入学科教育和教学,才是真正进入大多数家长、学生和教师所认可的校园,才能真正做到非遗传承与校园教育共赢。
第四、教育学和民俗学相关研究者应当关注“非遗进校园”的课程评价标准的建设,在现有的“戏曲进校园”“书法进校园”等框架相对完备的“某项非遗进校园”文件的基础上,拟定出非遗进校园整体的评价标准基本框架,结合各地的“非遗进校园”教育实践完善和验证评价标准的内容,让“非遗进校园”的效果可测、可知。当然,“非遗进校园”课程体系的研究、设计和实践是一个庞大的任务和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研究和实践,最终一定可以让非遗真正进入校园,进入学生的大脑和心灵里,达到文化传承和校园教育的双赢目的。